透过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在黑暗中拓展思维边界,绝境里谋求人类的自我拯救——长期以来,作为灾难片重要亚类型影片的瘟疫题材电影一直受到电影界的重视,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许多观众亦借机观赏此类电影,来增进对当下的理解,抚慰焦灼的心灵。4月23日,由我校影像传播研究中心、暨南大学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影视艺术中的‘疫’叙事”云论坛在线上举行,多位高校学者围绕瘟疫题材电影的思想、艺术等诸多面向进行了深入、专业的探讨和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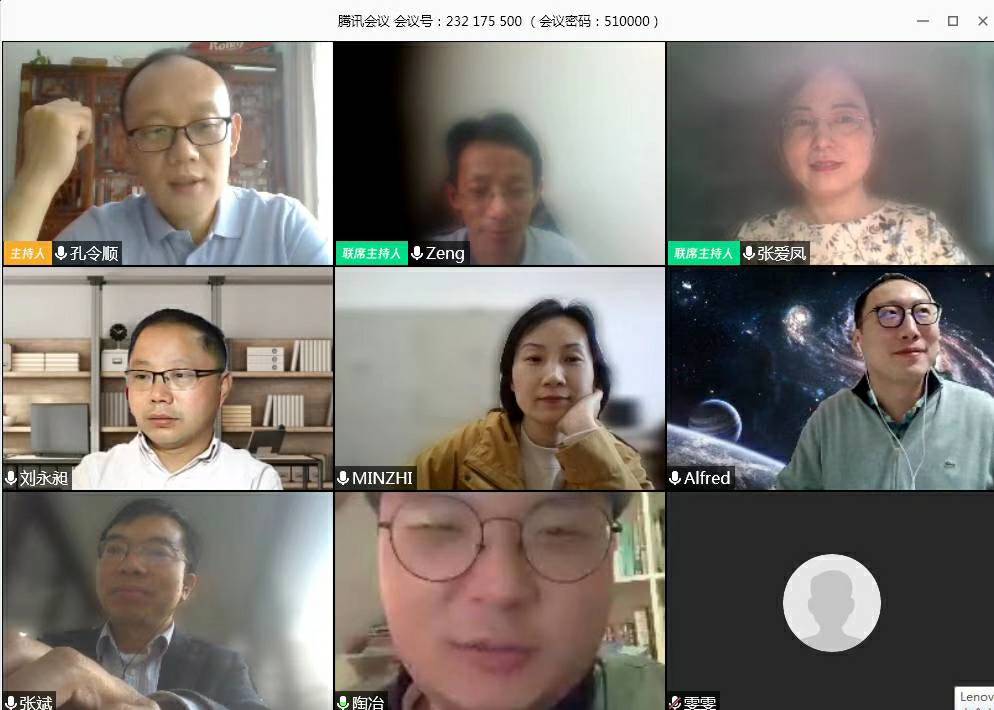
瘟疫往往来自对自然的入侵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早就精辟地指出,流行病是“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之构连的一个交界点”,暨南大学新传院教授曾一果则更加明晰地将瘟疫和各种传染病的根源定位于“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在他看来,许多瘟疫题材电影都在深层次上触及了全球化以来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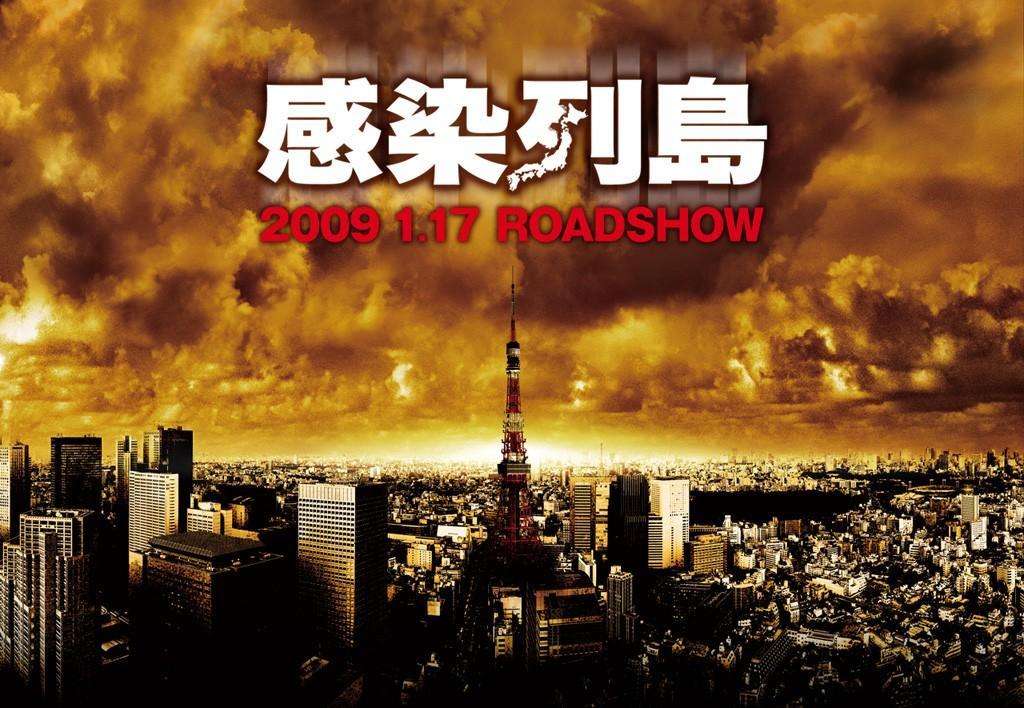
在《感染列岛》《釜山行》《传染病》等电影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病毒往往都是从动物开始传染给人,接着在某个地区蔓延,进而导致整个区域、城市和全球性灾难的发生。日本电影《感染列岛》就向观众展现了新型流感病毒在日本全岛疯狂传染的末日景象,为了寻找病毒源头,医生松冈君来到东南亚边陲小镇进行调查,终于发现病毒来自Minas岛洞穴中的蝙蝠身上,其真正根源是人类过度地砍伐森林、养殖鱼虾和开发旅游业等行为,导致了偏僻小岛的生态环境遭到污染,病毒由此产生。在观众更为熟悉的韩国瘟疫电影《釜山行》中,影片开头就是一幅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一头野生动物梅花鹿在郊区马路上被养猪人的车子撞死,车祸之后,死去的梅花鹿又奇迹般地复活为“僵尸鹿”。

“通过这些电影观众得以了解,大规模传染性流行病的传播表面看是由某个蝙蝠、梅花鹿或养殖场的鸡引起,追本溯源却是现代人类的破坏性生产和对自然的疯狂入侵所致。”曾一果说。
警惕瘟疫电影中的全球想象
如果将反省人类行为视为瘟疫题材电影的历时性维度,那么,全球化视野下围绕病毒和疫病展开的政治角逐、疾病隐喻,则构成了此类电影意味深长的共时性图景。上海大学教授张斌观察到,许多电影围绕病毒的起源与终结,由此蔓延开来的是关于“两个世界”的叙事,其中展开的全球想象值得人们思索和警惕。

在1976年由英国、意大利和西德联合拍摄的《卡桑德拉大桥》中,鼠疫病菌是美国秘密研制的生化武器,偶然被恐怖分子打破沾染并登上一列贯穿欧洲全境的火车。为了不让火车在欧洲(准确讲是西欧)停靠造成灾难,在美国麦肯齐上校的指挥下,列车开向了当时属于华沙条约国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小镇亚诺。在列车通过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时大桥坍塌,列车断裂成两半,一半坠入峡谷的河中,一半留在岸边。大桥的垮塌意味着悲剧不可避免,也象征着冷战双方的不可沟通性与非人道性。
不过,许多瘟疫题材电影并没有像《卡桑德拉大桥》那样表现对冷战思维的反思,而是有意或无意地与之达成了合谋。张斌认为,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的社会分工,这同时也是一种不平衡与不平等的全球政治权力关系,以好莱坞为核心的电影工业生产体系复刻了这种现实等级关系,在瘟疫电影中进行了想象性的反映。
最突出的表现是,瘟疫电影中的病毒一般大多起源于全球生产链条的下游国家,而抗击瘟疫最重要的抗体疫苗的研制工作往往由代表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美国最高级传染病研究室进行研制,在全球性危机事件中扮演着拯救人类种族生命的主导力量。这样一种电影霸权叙事亟待受到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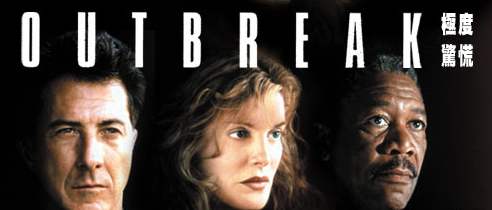
例如,《极度恐慌》中的莫塔巴病毒源自非洲白面猴,《传染病》中猪流感来源于处于初级加工环节的香港贫困村庄,《流感》中的初始禽流感病毒携带者是从香港向韩国偷渡寻找美好生活的东南亚人。另一方面,《极度恐慌》中主人公和他的妻子都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实验室工作,曾经在全球各地面临重大传染病威胁的时候提供美国的公共帮助;《我是传奇》中罗伯特·奈佛作为美国军方的病毒学家,在绝大部分人类感染失活变成黑暗猎手之后,仍然执着地研发疫苗拯救人类。《传染病》中,也是美国科研人员最先研制出疫苗并自愿进行人体实验。在这些影片中,西方电影人的“救世主想象”显示是偏颇的。
疫情面前,如何建立新的世界团结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永昶注意到,瘟疫题材电影中,连绵不断的感染与死亡,争分夺秒的追查与抢救,病毒的速度,叙事的速度,镜头的速度,此起彼伏交织呼应,进而形成了令人窒息的沉重的戏剧张力。在采取加速化的叙事节奏的同时,导演同时对时空进行充满意味的剪裁组合,闭合叙事成为典型的时空呈现方式:《12只猴子》人类在地下建造的躲避灾难的“诺亚方舟”以及穿越者被禁闭的精神病院,《极度恐慌》中面临被完全消灭危险的小镇,《传染病》中被军警封锁的城市街巷,将这种闭合叙事推向其极致与高潮的典型案例,则是《卡桑德拉大桥》与《釜山行》这两部影片中呼啸前行的火车。在这列火车上,人性的光芒与黑暗,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在闭合叙事中残酷斑驳地呈现,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检验室。

在对美国疫情灾难电影的分析中,122cc太阳集成游戏副教授姚睿发现,此类电影通常呈现出描述当下困境的“进行”时态、感染后变异丧尸的“假定性”时态与展现末日浩劫的“后启示录”时态等三重时态。“进行”时态的影片展现了病菌/瘟疫的传播与扩散过程,表现医生/科学家和普通民众与政府/军队的对抗与合作,呈现出动作片的视觉风格。“假定性”时态采用了人类感染后会变异为嗜血丧尸的假定性设置,它是现实世界的“平行宇宙”。“后启示录”时态是疫情传播的“完成时态”,描述瘟疫灾难摧毁人类文明后呈现的可能未来。
然而,极力地复刻灾难并不是电影表达的最终目的。刘永昶发现,习惯好莱坞戏剧方式的大部分导演都不会允许纯粹的悲剧性终结,于是,适当的叙事减速,让镜头间或慢下来,可以让人与人之间温润的情感恰到好处地汩汩流出,成为冷酷无情的病毒的参照系。《12只猴子》 里时空穿越者与精神科医生的逐渐心心相印,《感染列岛》中两位医生之间默默相守难以言说的爱情,《流感》中母亲对患病女儿不离不弃的守候,《釜山行》里父亲为女儿纵身一跃的决绝牺牲,都能直击观众们最柔软的内心。这些动人的时刻,通过慢镜头或是镜头的重复强调,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大体相等,甚至更为延宕,这让观众们可以获得暴风骤雨冲击后的心灵休憩。这显然不是在宣告粗糙莽撞的“人定胜天”,而是在或隐或显地暗示,支撑人类这个命运共同体度过无数历史劫难的,是让人与人之间紧密连接的爱。

陕西师范大学新传院副教授王敏芝则通过分析韩国电影《流感》,聚焦瘟疫题材电影中被隔绝的“他者”和最终的回归之路,警示人们留意随着病毒流行,受感染者首先被视为异类,甚至会直接被视为病毒本身。瘟疫里生成的“他者”们会以什么样的路径被接纳为“我们”,是影片的终极追问。
“在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中,人类正站在一个关键时刻:是不断强化‘他者’视角还是不断建构‘共同体’信念,可能直接塑造着人类未来的命运。”王敏芝说。问题随之而来:疫情之中以及疫情之后,我们如何重新建立某种新的世界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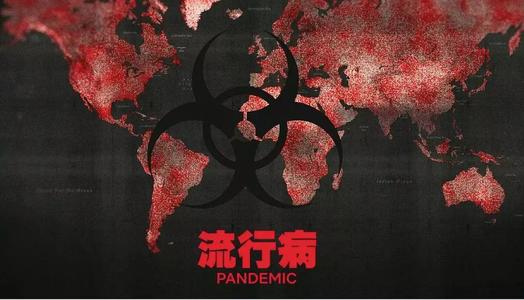
诉诸科学亦是“面对疫情,人类何为”的应有之义。我校新传院教授张爱凤重点分析了美国六集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简称《流行病》)中的科学传播。纪录片《流行病》于2020年1月22日在Netflix上线播出,豆瓣评分8分。该片从政府公共卫生决策、公共健康防御体系、医疗救治体系、病毒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多元化的视角来聚焦流感,采用平行叙事的方式记录了全球不同地区的科学家、医护人员与病毒作战的经历和故事,对观众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科学传播。纪录片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培养有反思的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的使命与责任。张爱凤提示,当下,由于在监测病毒传播、控制疫情扩散方面缺乏科学的预防理念和积极的准备措施,导致疫情在一些国家处于失控状态,付出了沉痛的生命代价,在这样的背景下,《流行病》或许可以启发思考。
一如拉图尔所所言,与病毒的斗争,是为下一次的环境危机做预演。电影是想象的,但不是假的,而是一种隐喻和预演。通过欣赏优秀的瘟疫题材电影作品,观众们可以从中窥见电影人的镜像折射和态度表达。但愿,瘟疫电影的过去想象不是我们的未来实景。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